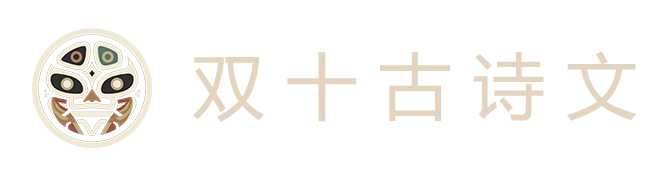韦曲花无赖,家家恼煞人。
绿樽虽尽日,白发好禁春。
石角钩衣破,藤枝刺眼新。
何时占丛竹,头戴小乌巾。
野寺垂杨里,春畦乱水间。
美花多映竹,好鸟不归山。
城郭终何事,风尘岂驻颜。
谁能共公子,薄暮欲俱还。
韦曲花无赖,家家恼煞人。
绿樽虽尽恼,白发好禁春。
石角钩衣破,藤枝刺眼新。
何时占丛竹,头戴小乌巾。
野寺垂杨里,春畦乱水间。
美花多映竹,好鸟不归山。
城郭终何事,风尘岂驻颜。
谁能共公子,薄暮欲俱还。
韦曲花无赖¹,家家恼煞(shà)人。
¹无赖:《汉·高帝纪》:“始大人常以臣亡赖。”注:“江淮之间,谓小儿多诈狡狯为亡赖。”
绿樽虽尽日,白发好禁春。
石角¹钩衣破,藤枝刺眼新。
¹石角:《仇池记》:石角外向。
何时占丛竹,头戴小乌巾。
野寺垂杨¹里,春畦(qí)乱水间。
¹垂杨:《三辅黄图》:长杨宫中有垂杨数亩。
美花多映竹,好鸟不归山。
城郭终何事,风尘岂驻(zhù)颜。
谁能共公子,薄暮¹欲俱还。
¹薄暮:《淮南子》:“薄暮而求之。”注:“薄,迫也。”王嗣奭曰:大抵高人贵介,所好不无浓淡暄寂之殊,如陶学士以取雪烹茶为清事,而党太尉以销金帐下浅斟低唱为乐事,然不知其为伐性之斧斤也。“风尘岂驻颜”,所以箴之者至矣。
韦曲花无赖,家家恼煞人。
绿樽虽尽恼,白发好禁春。
石角钩衣破,藤枝刺眼新。
何时占丛竹,头戴小乌巾。
野寺垂杨里,春畦乱水间。
美花多映竹,好鸟不归山。
城郭终何事,风尘岂驻颜。
谁能共公子,薄暮欲俱还。
这两首诗当依《杜臆》《杜诗详注》,作于唐玄宗天宝十三载(754)春天。当时杜甫仍在集贤院待制,一直未得到官职,心中抑郁,勉强陪贵公子饮酒作乐。虽有被捐弃的隐忧,但还没有完全失望,诗人还想通过友人的举荐或走“终南捷径”,以取得一官半职,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。杜甫陪郑潜曜在韦曲游玩,写下这两首绘景咏怀诗。一说,这两首诗作于唐肃宗乾元元年(758)春天。时任左拾遗的杜甫由于受到排挤,不得信任,倍感苦闷,经常去长安城南的曲江游览散心。一次游韦曲时,他写下这两首诗。
第一首写诗人面对韦曲春景,触动归隐之情。首联用俗语,说“花无赖”正见其有趣;说“恼杀人”正见诗人喜爱春光,反言以志胜,豪纵跌宕。颔联补足首联之意,韦曲的春色很好,这正是及时赏玩春光的时候,可是诗人的头发白了,青春已经消逝,不再有少年的游兴,所以对着春光有无可奈何的感慨。“白发好禁春”,仍然是用反话来透露正意,是说衰老的人不好当着这春光而尽情领略,可见“花无赖”“恼杀人”都是从感叹自己衰老的角度说的。颈联即寻幽兴,却完全是贬斥的口吻,说石角钩破衣裳,藤枝新刺眼睛。其实,诗人到处游览,饱领美景,新绿柔条令人眼目一新;走得匆忙,才致“石角钩衣破”。因而这些贬语,正是极度喜爱的反语,是愈痛而愈快之情。尾联故作问语,说什么时候才能占据丛竹,头戴乌巾,抒发了绝尘归隐的情怀。
第二首承接第一首而来,前半写景,后半抒情,亦别是一格。首联以野寺垂杨,春畦乱水,领韦曲胜景,即有羡慕村居幽事之意。颔联以美花映竹承胜景,而明言好鸟不归山,小鸟犹知恋幽居,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。颈联露出本旨,说城郭内尽是风尘,风尘中百般戕贼。杜甫在长安困居多年,所以有这样的感慨。由于郊游,得自然之趣,更增添了对城郭的厌恶。尾联反点作结,暗示出公子无忧无虑,尽情游乐,而诗人和其他陪游的人都不可能有那样高的兴致。诗人仕途坎坷,既欲激流勇退,又不忍拂衣而去,还要为生活奔走。诗中就表现了这种矛盾的思想。
参考资料
1、张志烈主编. 杜诗全集 今注本 第1卷[M]. 成都:天地出版社, 1999:431-432. 2、赵清新著. 唐诗札记[M]. 昆明: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14:135. 3、孙潜著. 杜诗全译 1[M]. 上海:东方出版中心, 2021:133-134. 4、凌朝汉著. 洗石集[M]. 拉萨:西藏人民出版社, 2006:126-128. 5、周振甫著. 诗词例话[M]. 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 1979:277. 6、徐应佩,周溶泉编著. 古典诗词欣赏入门[M]. 武汉:湖北教育出版社, 1990:178-179. 7、李志慧著. 杜甫与长安[M]. 西安:陕西人民出版社, 1986:75-76.